中本聰論文:美國如何侵蝕自由並重塑全球金融秩序?(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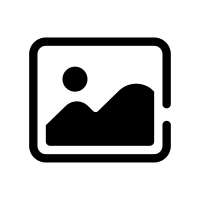
來源:Bitcoin Magazine;編譯:鄧通,金色財經
在美國,二十世紀始於權力的集中化,它用對聯邦權力的全新解讀取代了美國自由傳統的關鍵要素。1910 年傑基爾島會議的與會者起草了《聯邦儲備法案》,該法案於 1913 年通過成爲法律,從而成立了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美聯儲肩負着保持低通脹和高就業的雙重使命,其主要工具是控制貨幣供應量和通過聯邦基金利率控制貨幣價格。不久之後,1929 年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演變成我們稱之爲大蕭條的經濟危機,美聯儲受到了考驗。美聯儲既沒有阻止也沒有緩解這兩場危機,但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領導人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國家需要對美國經濟生活施加更多控制。美國隨後的威權主義轉向反映了其他國家的軌跡:1933 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FDR) 發布了第 6102 號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居住在美國的人將黃金上繳美國財政部,並暫停美元兌換黃金。他實施的資產沒收措施與同一時期其他威權主義領導人實施的措施如出一轍,其中包括溫斯頓·丘吉爾、約瑟夫·斯大林、貝尼托·墨索裏尼和阿道夫·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國的盟國用黃金購买美國制造的武器。這使得美國積累了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儲備。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聲時,盟國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开會,確定战後國際貨幣秩序的框架。他們決定將美元(再次可兌換黃金)確立爲全球儲備貨幣。同一次會議還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立,這兩個跨國貸款機構表面上的職責是促進和平衡國家間的貿易,同時促進國際發展,但其弊端卻包括將數十個貧窮國家卷入無法逃脫的債務奴役之網。
與此同時,在美國,战後軍事工業綜合體應運而生,它既確保了和平時期战時態勢的正常化,也確保了向盟國及其他國家進行軍售以提升GDP。战爭常規化是美國反共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始於朝鮮战爭,並延續至越南、老撾、黎巴嫩、柬埔寨、格林納達、利比亞、巴拿馬等國,更不用說在此期間發生的無數祕密行動和代理人战爭——必須以某種方式獲得資金支持。這一必要性促使尼克松政府於1971年暫停美元兌換黃金,並在幾年後與沙特阿拉伯政府達成非正式協議,以美元計價石油採購,並將這些美元重新投入美國經濟。這項石油美元協議雖然具有條約的特徵,但卻是由行政部門完全祕密達成的,部分原因是爲了規避憲法要求美國加入的所有條約都必須得到國會批准的規定。
隨着全球主要產油國开始以其他貨幣爲石油定價,石油美元體系本身正在瓦解。這是國際社會對冷战結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可預見反應,該政策一直堅持美國在國際貿易和軍事行動中保持單極主導地位。尤其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成爲美國宣布無限期反恐战爭、斥資數萬億美元發動對外战爭、重新軍事化或分裂那些原本會走向更加穩定的國家的借口,最重要的是,通過建立新的軍事司令部(美國北方司令部)和新的行政部門(國土安全部),正式軍事化美國本土。
國土軍事化——這在美國建國者眼中是極其不可接受的——意味着以反恐的名義,通過對一切事物實施反洗錢/了解你的客戶 (AML/KYC) 制度,扼殺公民最後一絲隱私權。這一發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70 年代,遠早於反恐战爭。事實上,20 世紀 70 年代可以被視爲銀行家革命全面成熟、美國自由實驗真正瓦解的十年。1970 年,《銀行保密法》在美國國會通過,拉开了 70 年代的序幕。該法要求美國金融機構保存所有“在刑事、稅務和監管調查或訴訟中具有高度實用性”(美國財政部解釋爲“在刑事、稅務和監管調查或訴訟中具有高度實用性”)的金融交易記錄,並根據執法機構的要求與其共享這些記錄。同樣,金融機構必須報告任何超過 5,000 美元的資金轉入或轉出美國的情況。隨後,財政部根據該法案頒布了一項規定,規定所有超過1萬美元的國內交易都必須報告。盡管即使按照保守估計,美元自1970年以來也已損失了近90%的購买力,但這一報告門檻至今仍未改變。
《銀行保密法》史無前例地削弱了憲法第四修正案中關於禁止無證搜查和扣押的保護。盡管受到質疑,最高法院在美國訴米勒案(1976 年)中維持了該法的原判,確立了第三方原則:美國人對第三方持有的記錄沒有合理的憲法保護期望。這一裁決令一些人感到意外和憤怒,這反過來又促使國會在兩年後(1978 年)通過了《金融隱私權法案》。然而,該法案對金融隱私權規定了 20 項實質性例外,最終進一步削弱了隱私保護。同年,國會還通過了《外國情報監視法》(FISA),其既定目的是在尼克松政府濫用職權之後,遏制聯邦情報和執法機構的非法監視行爲。然而,《外國情報監視法》聲稱要通過設立一個非法法庭,即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ISC)來實現這一目標,這是一個祕密法庭,可以對國家要求的幾乎所有監視活動籤發機密逮捕令。
《銀行保密法》(1970 年)、《美國訴米勒案》(1976 年)、《金融隱私權法》(1978 年)和《外國情報監視法》(1978 年)是當今美國政府全面監控體系的種子。這四項法律手段早在個人電腦或互聯網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之前就扼殺了美國的自由,但它們卻被用來爲全面收集和共享通過軟件平台和數字網絡(現代生活中幾乎不可避免的基礎設施)發生的金融交易數據(以及更廣泛的通信數據)辯護。它們還催生了至少八項額外的聯邦法律,大大擴大了合法監控的範圍:《洗錢控制法》(1986 年);《反毒品濫用法》(1988 年);《安努齊奧-威利反洗錢法》(1992 年);《洗錢制止法》(1994 年);《洗錢和金融犯罪战略法》(1998 年); 《美國愛國者法案》(2001 年)、《情報改革與預防恐怖主義法案》(2004 年)以及《外國情報監視法修正案》(2008 年),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第 702 條修正案,該修正案授權在獲得司法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的授權下,甚至可以規避外國情報監視法院。最後,這些法律和法律判決爲至少三個新的情報機構的成立提供了理由,這些機構的職責是收集和共享全球金融交易數據: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1989 年)、金融犯罪執法局(1990 年)和美國財政部情報與分析辦公室(2004 年)。
簡而言之,在一代人的時間裏,20世紀初已經集中化的美國銀行體系淪爲國家警察職能的延伸。華爾街、美聯儲和財政部之間的“旋轉門”——精英們在這些機構中輪換職位的職業循環——只會加速制定和執行法律的人與控制貨幣的人之間勾結的飛輪。這確保了這台最初由銀行家革命建造、後由石油美元體系支撐的機器,通過非正式協調和官方救助,爲精英們持續運轉。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各國民族國家採取的行動並未糾正任何這些錯誤。幾乎所有國家的銀行家都獲得了救助,除了像冰島這樣的例外。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他們和許多行業再次獲得了救助。在美國,這些救助計劃通過兩黨領導人支持的零辯論綜合法案獲得批准、續籤和資助。
但 20 世紀 70 年代不僅僅將銀行與國家合並並迎來金融隱私的終結;這十年還开創了緊急狀態統治,即美國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以便將憲法禁止的權力僭取爲自己所用。1976 年,國會通過了《國家緊急狀態法案》(NEA),該法案正式規定了總統宣布緊急狀態的程序。盡管表面上意在限制總統的緊急權力,但該法案在程序上非常精確且範圍非常廣泛,導致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頻率大大提高。1979 年,吉米·卡特總統根據該法律宣布了第一次國家緊急狀態——第 12170 號行政命令——在伊朗人質危機後對伊朗實施制裁。爲了做到這一點,他還援引了 1977 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該法案授權總統在認定任何美國境外實體構成“異常和特殊威脅”時,可以凍結該實體的資產並阻止其交易。
這兩項法律組合實際上賦予了美國總統單方面權力,只需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即可禁止和懲罰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的經濟活動。由於美元交易通常通過美國控制的金融網絡進行,且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商業記账單位和主權儲備貨幣,因此《國家經濟評估法》和《國際經濟權力法案》(美國國內法)一直被用來懲罰在美國管轄範圍之外運營的個人和組織。因此,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美國總統和美國財政部(負責執行總統關於金融交易命令的內閣機構)——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實施了一種有效的統治形式。
第12170號行政命令是美國首次通過行政命令對外國實施制裁。自此以後,行政命令已成爲美國總統繞過冗長的立法程序、快速實施制裁的常規手段。 《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始終與《國家緊急狀態法》同時援引,該法已使近七十項單獨的緊急狀態聲明合法化,制裁措施總計超過一萬五千項,且仍在不斷增加。此外,美國還利用其對聯合國安理會的影響力,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對特定實體及其相關實體實施多邊制裁;成員國隨後有義務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執行這些制裁。聯合國制裁的實施無需正當法律程序,許多目標實體從未被指控或定罪。制裁的實施輕而易舉,並且作爲一種懲罰和脅迫工具而廣受歡迎,表面上看對美國政客幾乎沒有什么負面影響,這促使制裁措施加速擴散。截至本文撰寫時,美國已對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國家實施了制裁。這些制裁的執行變得如此繁重,以至於財政部正經歷着創紀錄的員工流動率和難以應付的案件量。又一扇旋轉門出現了:財政部與私人法律、咨詢和遊說公司之間,前財政部官員利用他們對復雜制裁體系的了解和政府關系,爲他們的客戶爭取更好的政治和法律結果。
然而,或許最重要的是,制裁似乎對其所針對的政權幾乎沒有政治效果。除少數例外,專制政權依然存在,而受到制裁的民主國家往往會通過增加國防开支來應對,進一步鞏固現有政權的權力。受美國制裁的國家數量之多,促使數十個國家建立新的地緣政治聯盟,並建立能夠完全避开美國控制的銀行體系的替代金融體系。然而,事實證明,制裁的後果是常規化的貧困,甚至是經濟崩潰,這將影響受制裁國家的人民。這無疑會使受制裁民衆的內心和思想轉向反對美國,並在數十年內滋生怨恨和敵意。即使是針對特定行業或特定實體的所謂“智能制裁”,在政治上通常也是無效的;其範圍有限,對當權者的激勵薄弱,不足以產生足夠的壓力來迫使他們實現預期的政策改變或政權更迭。此外,這些制裁措施的實際實施往往對目標國產生雙重影響: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對那些事先做好規劃的強勢行爲體來說可能只是相對較小的麻煩,而武器禁運和對目標國商品出口的禁令則會造成比其預想的更大的附帶損害。這顯然令人質疑此類制裁是否能被稱爲明智之舉。
自 1970 年代以來,銀行——國家權力的鞏固存在着一種反常現象:上文所述的大多數立法都以限制看似不負責任的行爲者的權力爲表面公共目標而出台。《銀行保密法》旨在限制銀行的權力。《國家緊急狀態法》旨在限制總統的權力。《外國情報監視法》旨在限制聯邦執法和情報機構的權力。然而,所有這些嘗試都產生了與公衆預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因爲它們犯了一個根本性的致命錯誤:試圖通過法規來實現憲法框架中已有的限制。通過用聯邦法律凌駕於憲法之上,立法者創造了一種法律、政治和軍事環境,使政治假設回到了美國革命之前的狀態。主要的政治行爲體現在被理解爲國家;個人權利被重新概念化爲特權;個人現在在法律面前被推定有罪;如今,國家被視爲權利、金錢和權力的持有者,並以帝國主義和不負責任的方式運用這些權力。這些都是政治文化陷入深度危機的症狀。
標題:
地址:https://www.pressbased.com/post/12436.html



